西安股票配资公司 生活在巴黎:学习自由,赞美日常

7年前,栾颖新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去巴黎求学,专业是法国中世纪史。2020年,她找到了一种学术写作以外、用于自我讲述的声音。
她写在法语和母语间往返穿梭的经历;写她被陌生人插队时如何反击;写在街区里买菜、买面包、买烤鸡,与真实的人短暂而温暖的相遇;更多时候,她写的是巴黎给她的自由与包容。

不论什么季节,巴黎人都喜欢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晒太阳。(图/受访者提供)
这些经历组成了栾颖新2023年出版的随笔集《那个苹果也很好:在巴黎学会自由》。“在巴黎学会自由”或许有点夸张,栾颖新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她正在巴黎学习自由。
如果说《那个苹果也很好》是向内寻找之旅,栾颖新即将出版的新作《日常的启示:在巴黎知吃思》则更多关注外部世界。她写遍四季,从春天的芦笋、夏天的草莓,到秋天的栗子和冬天的时令甜点——它们与当地习俗、历史都有关。

《那个苹果也很好:在巴黎学会自由》,栾颖新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3
滤镜以外的巴黎
《新周刊》:你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法国中世纪史。你对法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栾颖新:我最初对巴黎的兴趣或许与哈尔滨被称为“东方小巴黎”这件事有关。我在哈尔滨出生、长大,因此对巴黎感觉既好奇又亲切。我上高中时常去黑龙江省图书馆,那儿有不少关于法国文学和历史的书。我就是在那儿借到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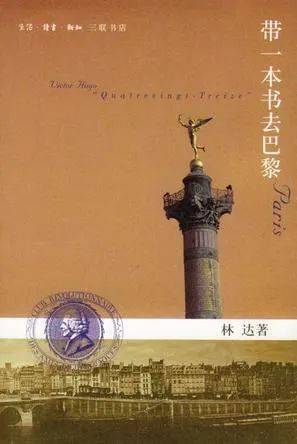
《带一本书去巴黎》,林达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8
我大学读的是历史学系。大一的第一节课是世界史通论。那是一门三位老师合开的课程,而给我们上第一讲的正是一位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老师。他在那堂课上引用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一句话。我不记得他具体引用的是哪一句话,但我记得他先读了中文译文,又读了法语原文。
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法语,我觉得法语的发音很好听。法国大革命史也让我着迷。我因此想学法语,想研究法国历史。我读本科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外国语学院联合开设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因为这个新专业,我得以在学习法国史的同时学习法语。
《新周刊》:正如你所说,巴黎是一座集中了诸多误解与幻想的城市。近些年,人们似乎正在对“滤镜下的巴黎”祛魅。你觉得巴黎或者说法国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吸引力下降了吗?
栾颖新:如果“滤镜”指的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让人产生的印象,那么不用“滤镜”看待巴黎是一件好事。我相信不论是居住还是旅行,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和体会,才能跟这座城市当下的、真实的一面产生联系。

从蓬皮社中心俯瞰巴黎。(图/受访者提供)
对某种文化是否感兴趣,可能并不取决于该种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何种文化感兴趣可能与个人认同和向往的东西有关。我想起日本摄影师星野道夫的经历。他离开日本,搬去阿拉斯加,拍摄阿拉斯加的动物和风光,最后在阿拉斯加去世。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提起他最初对阿拉斯加的兴趣:“大一那年,我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去阿拉斯加了。为什么是阿拉斯加呢?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能我潜意识里有一种对北极圈大自然的朦胧向往吧。”
《新周刊》:在外留学的生活时常会让人产生一种漂泊感。“漂在巴黎”的7年里,你是如何应对这种漂泊感的?是否有某个时刻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了?
栾颖新:我其实并没有体会到“漂泊感”。从我到巴黎那天起,我就是巴黎的一部分。在巴黎生活是我主动做出的选择。我从上本科时就很向往巴黎。能在巴黎生活对我来说是实现了一个愿望,我很开心。

栾颖新在艺术桥上与塞纳河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巴黎生活没有烦恼。巴黎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常常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奇迹。我被丰富的文化生活滋养,我觉得我能做成我想做的事。
巴黎一直在变
《新周刊》:你曾说,巴黎一直在变,而你想写的是现在的巴黎。《那个苹果也很好》收录的文章主要写于2020—2021年间,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此后你目睹了巴黎怎样的变化?
栾颖新: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认为巴黎这两年最明显的变化是通货膨胀。日常消费品和能源的价格都在持续上涨。

圣叙尔皮斯教堂前的广场。巴黎已经入夏。(图/受访者提供)
巴黎地铁近两年一直在施工。以地铁4号线为例,为延长已有线路和给地铁站的月台安装屏蔽门,该线路经常在周末和工作日的夜里关闭。
2020年至2021年,巴黎因疫情经历了多次封禁,当时地铁和公交的班次大幅减少。而地铁和公交的班次并没有随着封禁措施的取消而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坐地铁时很明显地能感觉到地铁比疫情之前挤。
巴黎近两年的另一个变化是自行车道在变多。骑自行车出行比以往方便很多。巴黎的共享单车系统叫“自由自行车”(Vélib’),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在我家附近就有好几个带桩的自行车存取点,十分方便。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尤其是晚上汽车不多的时候。骑自行车有一种不同于走路的速度,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骑车时,感觉自己在风里,格外自由。因为自行车,我觉得我跟这座城市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觉得很多地方都离我很近。

站在先贤祠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奥运进行时”的巴黎和平日有什么不同?奥运氛围浓厚吗?你有看比赛的计划吗?(编者按:本文采访于巴黎奥运会举行前完成)
栾颖新:因为奥运会开幕式和一些比赛将在塞纳河沿岸举行,7月中旬以来,河岸附近的街道安装了一些围栏。进入靠近河岸的特定区域还需要出示提前申请的二维码。河岸附近的一些地铁站在开幕式前一周到开幕式当天关闭。法国政府从今年春天开始鼓励大家奥运期间在家办公。我认识的一些人选择在奥运会开始之前离开巴黎,等奥运会结束以后再回来。
巴黎的奥运氛围很浓。很多公共建筑的外立面都有奥运主题的装饰。不少文化机构从今年春天开始举办与奥运会和体育相关的主题展览。地铁车厢里的线路图用粉色贴纸标出了举行奥运比赛的场馆。
我不去看比赛,没有买票。我打算看开幕式直播。

巴黎市政厅外立面,挂起了奥运会主题的装饰。(图/受访者提供)
7月26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1834.21万元,占总成交额20.4%,游资资金净流出1057.58万元,占总成交额11.76%,散户资金净流出776.63万元,占总成交额8.64%。
7月26日的资金流向数据方面,主力资金净流入3980.93万元,占总成交额14.67%,游资资金净流出2478.65万元,占总成交额9.13%,散户资金净流出1502.28万元,占总成交额5.54%。
《新周刊》:这两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在巴黎“常规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栾颖新:我从去年春天开始规律地游泳。差不多每两天去一次。巴黎有很多市立游泳馆,单次票票价十分合理,可以无限畅游的季卡更划算。最开始我最多能游500米,后来朋友鼓励我挑战1000米。去年秋天,我第一次游到了1000米。
身体的进步如此明显,我游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稳。我在游泳的过程中感到快乐。在泳池里一趟一趟地来回,听水的声音,放空大脑,或者思考一件事,都很好。游泳让我感觉放松。我明显感觉身体变得有力。我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并且在自己的身体里感觉很好。这种好感觉也对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每次游完1000米离开泳池,我就觉得世界上没什么可怕的事。
如今,“常规的一天”属于一种奢侈,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稳定。我来描述一下理想的一天吧。这样的一天每个月大概会出现一两次。
理想的一天的先决条件是没有日程安排,没有必须要见的人和必须要做的事。早上睡到自然醒,冲咖啡,吃涂了半盐黄油和果酱的面包。上午在家看书或写东西。写得饿了就去做午饭。煎鸡胸肉,煮鸡蛋,拌一大盆有很多蔬菜的沙拉。饭后困了就午睡,不困就不睡。下午去公园散步和晒太阳。回家路上逛书店,翻翻新出的书,买到一两本喜欢的。采购食物,买到新出炉的传统法棍面包。回家一边做晚饭,一边听广播。晚饭后窝在床上看书,困了就钻进被子睡觉。

卢森堡公园让人感到平静、放松。(图/受访者提供)
能这样自由支配的一天,堪称被魔法笼罩的一天。每次经历都很感激。而其他的日子也没那么糟糕,每天我都试着把理想的一天的组成部分塞到眼前的这一天里。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很不错。
“翻译时,我被文本穿过”
《新周刊》:你之前翻译了安妮·埃尔诺的《年轻男人》和《写作是一把刀》。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你会考虑作家的语言是否和自己契合吗?“在两种语言中穿梭”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你而言,哪一个更困难或更享受?近年来,不少华裔写作者在国际文学界崭露头角,你有考虑用法语写作除学术论文外的内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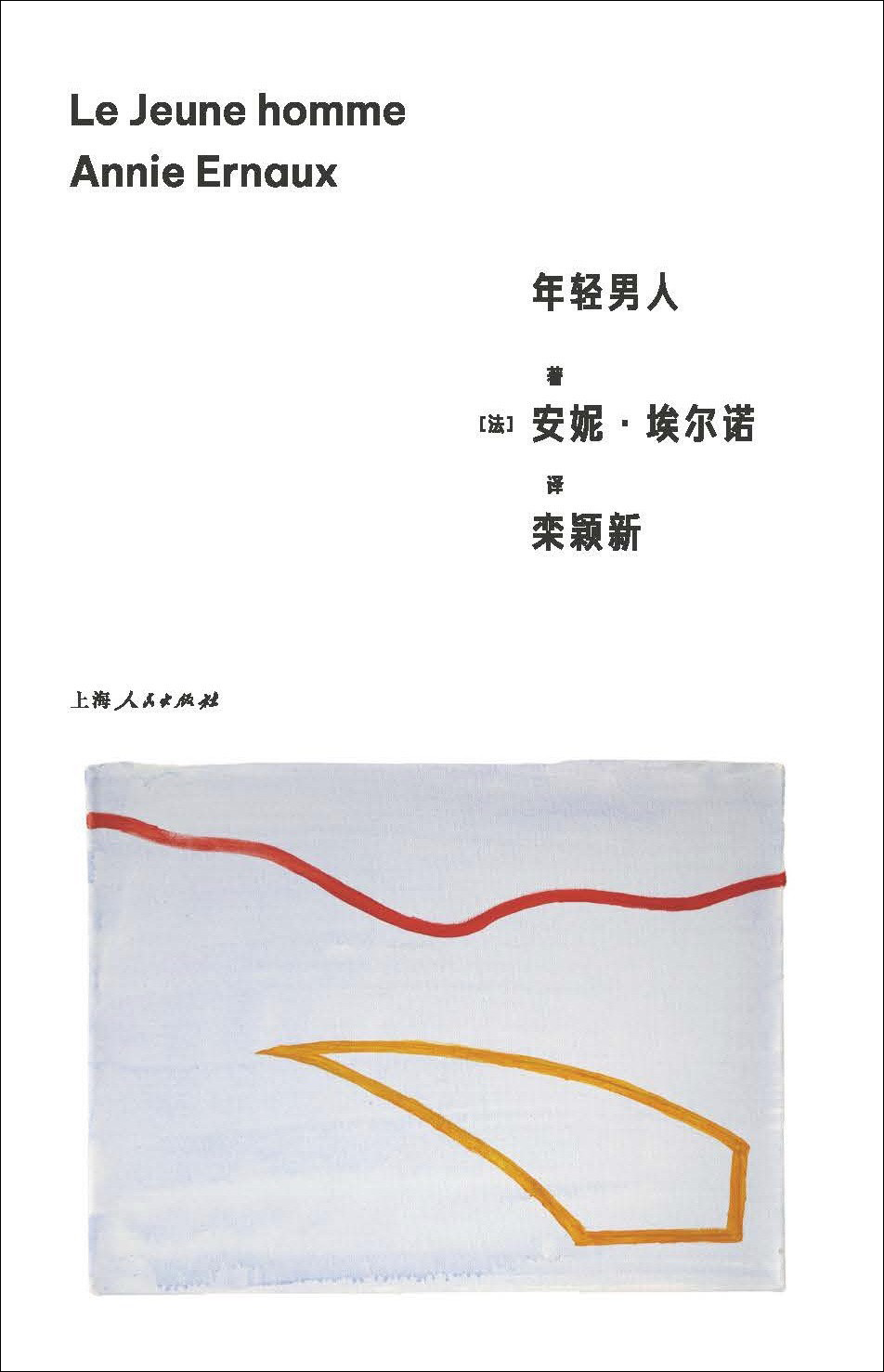
《年轻男人》,[法]安妮·埃尔诺著,栾颖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7
栾颖新:我翻译埃尔诺的书,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埃尔诺的作品。我希望我喜欢的书能被更多人读到。我之前翻译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也是这样的心情。翻译是一种分享。
《写作是一把刀》和《年轻男人》虽然都是埃尔诺的作品,但风格并不相同,埃尔诺在这两本书中的语气也不一样。而翻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试图抓住并且在另一种语言中还原这种语气。
翻译《写作是一把刀》时,我发现我在中文里能找到一种适合传达埃尔诺在这本书中的表达的声音。当时我觉得非常幸运。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我来自她。我先是她的读者。我认同她对文学的理解,欣赏她的追求和尝试。她对词语的态度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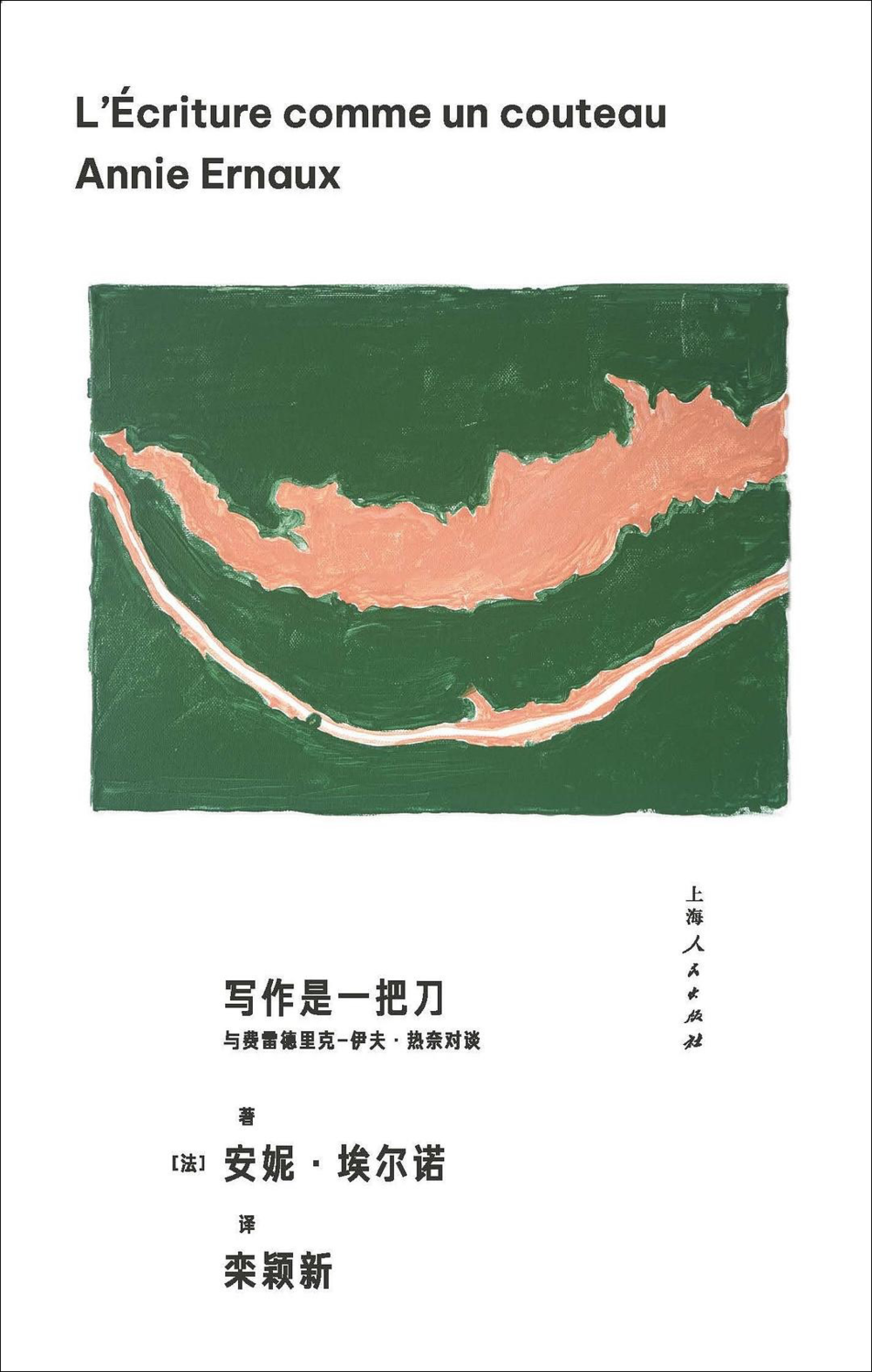
《写作是一把刀》,[法]安妮·埃尔诺著,栾颖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8
翻译的过程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是译者在处理文字,另一方面文字也在译者身上起作用。翻译时会进到文本的深处,进得比单纯阅读时深得多。而从那里出来时,自己已经被改变了。翻译时,我被文本穿过。翻译和写作我都喜欢,这两件事都让我感到快乐,两者相互促进。
我会用法语写作,我有写作计划。
作者:陈茁西安股票配资公司
